金庸小说《神雕侠侣》里面有这样一个情节,郭芙纠结到底喜欢修文、修武俩兄弟中的哪一个,杨过补刀:“两个都爱就是两个都不爱”。好多事情也都是这样的,如果一个事情两个相反的观点争议很大,那可能两种观点都不对。
关于现在社会的割裂,有众多的感慨,无论从哪个角度说,估计都会遭来骂声一片,但还是忍不住想说点什么。我们依旧说古,不为借古讽今,只是想与大家一起回忆这一段往事。
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桩公案,从一千多年前的北宋一直到今天,依旧是各家说各话。赞成者认为要是王安石变法能成,北宋富国强兵,平西夏,据辽金,华夏文明将不会遭受后来异族入侵的苦难。反对者认为,正是王安石变法毁坏了国家的统治基础,造成流民四起,国力疲惫,才给异族可乘之机。
易学大师邵雍的儿子邵伯温在《邵氏闻见录》里有段记载,说有次程颢来见王安石,王安石谈到推行新法有阻力,他儿子王雱在一边插嘴说:“把韩琦、富弼的头砍下来挂到集市上,新法就可以推行下去啦!” 程颢和邵雍在一条巷子里住很长时间,邵伯温听长辈们说的,还是基本可信的。
手里拿把锤子到处都是钉子,在变法派的眼里,只有震慑反对派才能顺利实施新法。这种思想随着党争加剧演变到极致,就出台了离谱的“元祐党籍碑”。将反对变法或者是被认为背叛变法的309人刻在刻在碑上,并要求全国各地复刻。 列入名单中的人还在世的要囚禁或者贬谪,已过世的人要拔除官衔,他们的子孙永远不得为官,皇家子女也不得与此名单上的罪臣子孙后代通婚,已订婚的要奉旨取消。
变法派强硬不近人情,反对派也固执不懂变通。就以不能完全归于旧党的折中派苏轼为例。在新法实施初期,苏轼给皇帝上万言书,历数古今得失,认为变法不可再行,却一直没得到回应。后来神宗皇帝下了一道诏书,严禁强推青苗贷款。算是一个补丁,针对的也是当时最大的漏洞——官僚阶层为了政绩强推青苗贷。面对皇帝对变法的修订,苏轼依然不依不饶,上书引用孟子的话,说一个偷鸡贼想要改过自新,决定每月只偷一只鸡,以此来讽刺朝廷这种五十步一百步的改进。
变法初期,王安石借助神宗皇帝绝对的信任,将旧党一干人等贬到地方去做官。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,旧党主政的地方,消极怠工,机械推进新法;新党主政的地方为了快速取得效果,不顾实际,强力推行,造成弊端连连。
在皇帝心里,西夏、契丹边患不断,国库空虚,官僚体系效率低下,亟需改革。旧党提出的都是大而化之的概念,新党给出的是具体的路径,怎么选择可想而知。在新党人士心里,没有旧党人士的阻挠,有序推进,新法必成。在旧党人士心里,新党不顾体统,结党营私,与民争利,祸乱天下,必须全力铲除。
那么,两党有没有共识呢,其实在施政目的上没有大的分歧,都希望国富民强,都希望政通人和,都希望外御强敌。争议的只是到达这个目的的方法。渐渐,这个初心已经不再有人提起,争执聚焦在实施不实施新法上,来回折腾。
在这个时期,活跃在帝国舞台上的有欧阳修、范仲淹、司马光、富弼、韩琦、王安石、苏轼等等,他们有着极高的政治智慧和个人操守,是中国古典史上最群星闪耀的一个时期,变法后四十年不到,伴随着党政各种戏码上演,帝国的家底被一点点掏空,留给了后世无限唏嘘的靖康之变。
回到开头,当两种观点纠结不下之时,说明这两种观点都不是最终的答案。真正达成一致很难实现,这大概是人类组织的悲剧所在。功成不必在我是一种多么稀缺的觉悟,更多的是不是由我主导的成功宁愿失败——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先见之明。
委屈就全是一种极高的智慧,却往往遭受非议。一意孤行者表演着自己的高明,在大厦倾倒以后哀痛自己的观点不受重用,持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,这也是悲剧所在。
振臂疾呼或者惨痛教训都不足以掀起一丝波澜,粗浅的文字更不足以撬动认知的天平,真理是惨白无力的。大道至简,高明的忽悠——信仰,伪装在其他方向里的目的,将争名夺利者推上前台,事成之后享受孤独与落寞,这才是英雄本色。
© 版权声明
THE END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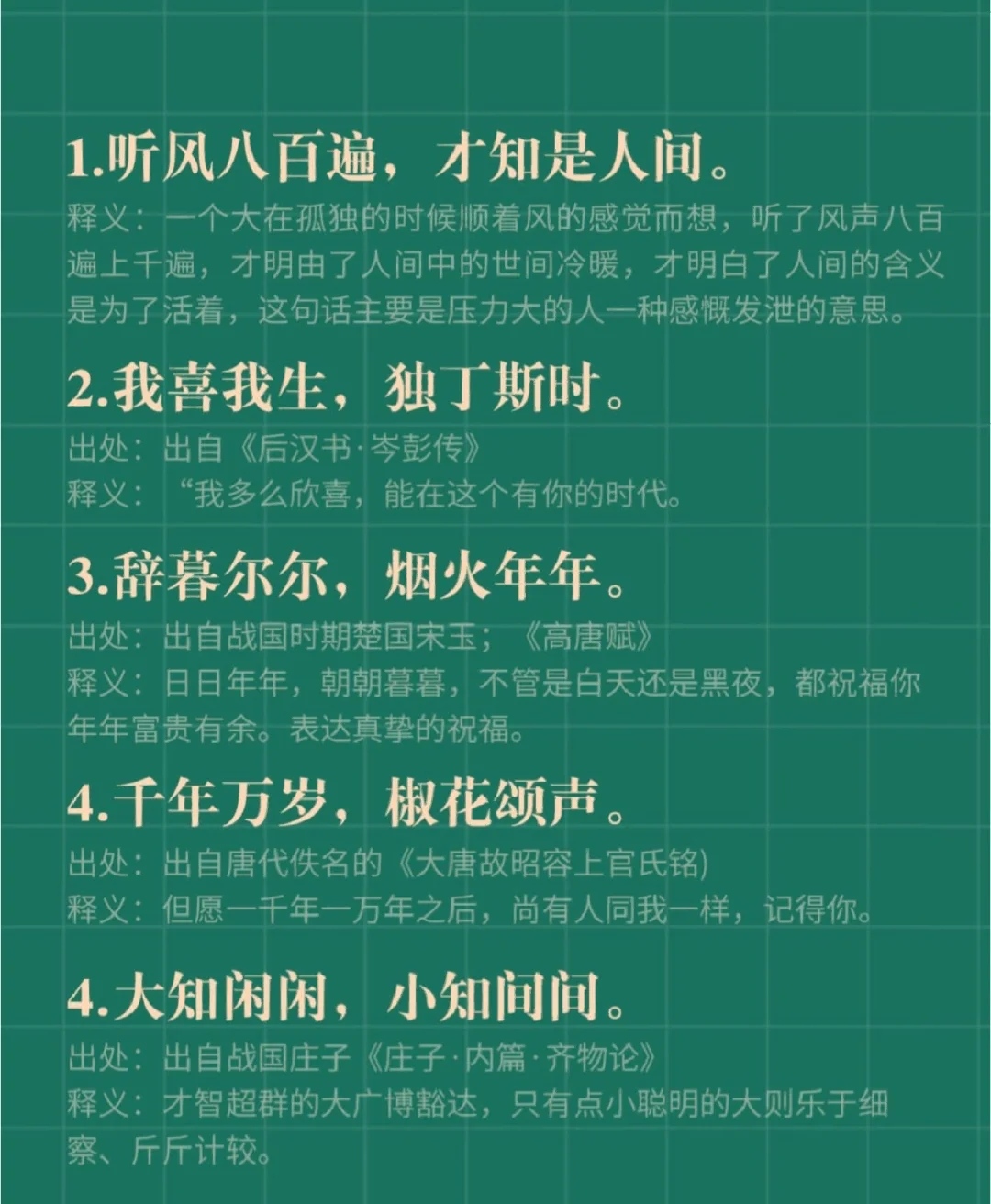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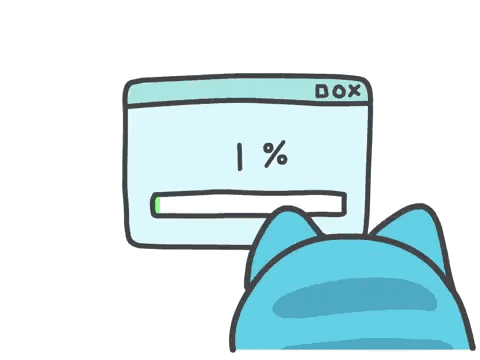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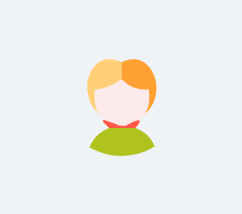


暂无评论内容